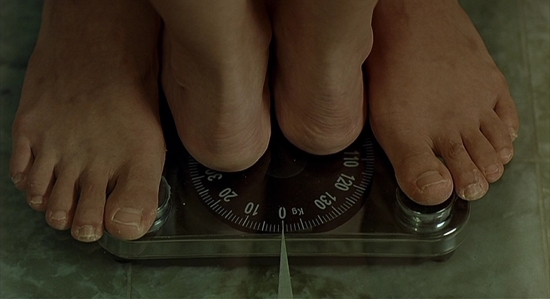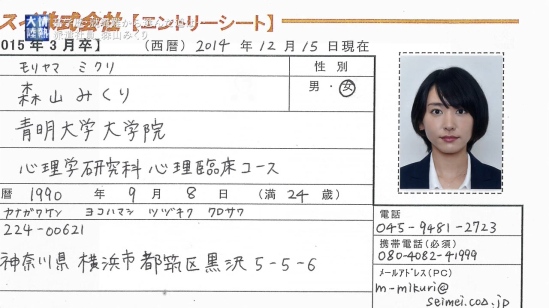《大象席地而坐》:胡波的悲觀主義宣言書/張智琦
金馬獎最佳影片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最近在院線上映,引發不少討論,長達近四小時的片長,考驗著觀眾的耐性和專注力,而導演胡波的自縊,更讓這部遺世之作添上一絲傳奇色彩。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探討的主題並不困難,而且相當具有普世性(特別是在現代原子化的社會中),過去已有許多文學家、哲學家和藝術家用不同的方式闡述過,一言以蔽之就是「人的存在是痛苦的,世界是悲慘可怕的,生命是不值得活的」。悲觀主義、存在主義、虛無主義的思想都是在講這件事,宗教則試圖為人生的苦痛給出一條救贖之路,但在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中,胡波要展現給我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,顯然是最絕望、最黯淡無光、沒有出路的一種,印象中似乎不存在這麼一部宣揚悲觀思想的中國電影,這部片因此注定有它的特殊價值。

從片中可以看到,胡波對人的存在的理解是徹底悲觀的,電影始終沉浸在灰色調中,角色總是一臉陰鬱的走在鏡頭裡,人與人的關係充滿疏離、爭吵、衝突、欺騙、暴力、無法理解、相互傷害…,四位主角們的家庭關係、同儕關係和愛戀關係都是破裂、失敗的,當鏡頭隨著小狗被咬死的老頭到了老人院,那一個個猶如關在小房間中「等死」的老人們,也映照出人的存在本質上的孤獨和悲哀。
不過,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可貴之處在於,它不是一個徒有概念、「強說愁」的悲觀主義作品,而是盡可能做到情節寫實、人物情感飽滿,以中國北方小鎮為背景,訴說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。因而電影要傳達的悲觀哲學,首先是來自一個個具體的生活經驗,青年的壓抑和爆發、母親的歇斯底里、老人吐出的無奈,都是源自生活的難堪和活著的艱難,讓他們一個個坐困愁城,乃至離家出走。儘管有些地方,人物的對白仍有過於文藝腔的問題,甚至不必要地在台詞中把主題直接明講出來,但我想整體而言還是瑕不掩瑜的。
我特別喜歡幾個對手戲的鏡頭,是關於人們互掀底牌鬧翻卻也是坦誠相對的時刻,比如男孩向另一個男孩坦承他偷了手機、老師和學生的不倫東窗事發、女孩向母親表明她和老師有染,然後演變成崩潰和決裂。在胡波的凝視裡,我們發現在親密的人之間,原來彼此是深刻的不瞭解甚至憎恨,反而在混混和男孩的生死對峙的一刻,我們看到交流知心的可能。
看這部片前最令我困惑的問題是,這近四小時的片長是否必要?(或許我們該慶幸電影裡幾個主角都長了個好看的臉,即使看著鏡頭跟著他們的後腦勺和喪臉走來走去,也不會讓人感到沉悶)在觀影過程中,我也會想胡波的電影要傳達的道理,或許用一首詩就可以講完,但看完後覺得,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長度的確是必要的,沒有這樣貼著四個主角跟蹤一日的紀錄,我們就無法回過頭直視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的各種破事,沒有辦法真正體會胡波一再想告訴我們的「人生是片荒原」、「這世界太噁心了」、「我什麼也不會」、「去哪裡都一樣」…。
問題是,在認清這一切後可有希望?片名的「大象」顯然是個隱喻,當結尾眾人踏上往滿洲里的路,為的是看那頭傳說中「席地而坐的大象」,這大象意指的可以是「希望」、「烏托邦」、「活下去的動力」…等等。但最後一幕卻停在了旅程半途,眾人下了深夜熄火的巴士,男主角和其他乘客在車前踢毽子(前面說男主角擅長踢毽子,但看起來踢得不很好呀),然後黑暗中陡然傳出一聲聲象鳴。
沒有大象,卻有象鳴;人在半路,還未抵達…我想,胡波並沒有給我們一個他本來就不認為有的希望,但那或許還是一個值得追尋和活下去的理由。

***本文首發於苦勞網,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。***